科学家正致力于使用T细胞疗法成功治疗癌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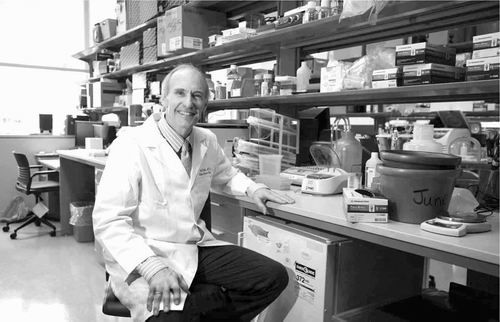
Carl June和其他人正致力于使用T细胞疗法成功治疗癌症。然而这条路起起伏伏,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一个下午,肿瘤学家Carl June和David Porter坐在美国佩雷尔曼先进医学中心内的一家咖啡馆里。这座玻璃和钢制的建筑坐落于宾夕法尼亚大学。
June和Porter面临一个问题。2010年夏季,他们治疗了3位已别无选择的白血病患者。在一个细胞疗法实验中,患者自身的T细胞在实验室中经过基因设计,可以在患者身体中增殖,寻找并破坏癌细胞。
该策略的效果超出了医生的最大期望,它消除了每个患者身上数磅的肿瘤。
为3位患者生成细胞共花费35万美元。目前科学家缺乏钱和“载体”——他们利用残缺的艾滋病(HIV)病毒将新基因插入T细胞。于是研究人员向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(NCI)及其他机构寻求资助以继续临床试验。Olson和另一个患者身上的肿瘤消失不见。第三个人只有部分反应,之后因疾病去世。资助者认为这种疗法太过实验性和不切实际。Porter和June无功而返。
啜饮着咖啡,Porter和June考虑着下一步计划。“我们决定发布仅有的这3位患者的数据。”June说。Porter勇于尝试,但也怀疑没有知名期刊会接收只有3个受试者的论文。
结果证明他是错的。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接受了关于Olson和他的相当于老鼠剂量T细胞的报告。《科学—转化医学》抢下了所有3位患者的详细文稿。2011年8月,论文同时出版。一时间他们名声大噪,June收到5000份患者及家庭的请求,他们希望参与这种疗法实验。
NCI决定在4年里每年资助June小组约50万美元,部分用于为患者制造T细胞。制药公司也向June及同事伸出了橄榄枝。
两年之后,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都渴望改造T细胞,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例如,该疗法仅能够治疗白血病的一个子集,并且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36位患者以及其他地方的50多位患者,接受了这种疗法。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,很多人出现了严重副作用。即使那些疾病消失的患者,也不清楚这种平静能持续多久。
目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,如何推动工程T细胞疗法进一步发展——如何在更多患者、更多研究中心、更多不同类型的癌症中试验它。马里兰NCI外科肿瘤医生Steven Rosenberg说,药品公司“不在乎花费5亿美元开发第一瓶药,只要你能用1美元制作出第二瓶”。
T细胞改造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以色列免疫学家Zelig Eshhar正在美国帕洛阿尔托市度假,他在考虑一个非正统的问题:作为免疫系统的哨兵,T细胞是否能被诱导破坏不同的目标。要完成这一工作,Eshhar认为他需要T细胞认出和抓住那些它们常忽视的分子。而唯一方法是在T细胞中插入外来DNA,从而改变它们产生的受体。
Eshhar返回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开始研究。失败接踵而至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,Eshhar取得成功,他将一种综合基因序列加入到一种容易接受外来DNA的永生T细胞中,使这些细胞能杀死新目标。
Eshhar的壮举只是第一步。要治疗类似癌症的疾病,研究人员需要鉴定某些肿瘤细胞的唯一蛋白质目标,否则这些改良过的T细胞将破坏健康组织。他们也需要确保T细胞在体内繁殖,持续摧毁癌症的每个迹象,并防止复发。
慢慢地,少数研究人员注意到Eshhar的成就,并开始推进。纪念斯隆—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细胞治疗学家和肿瘤学家Michel Sadelain着手将基因引入人类T细胞中。“我花了三四年才更好地将基因转移到超过0.5%的培养物中。”Sadelain说。
Sadelain一开始便关注癌症,相比之下June到达这一领域的道路更加曲折。他的职业轨迹沿着冷战的历史发展。1971年,他放弃入读斯坦福大学,转而进入海军学院。越南战争结束2年后,June选择留在军队,继续其医学学习。
随着对核攻击的恐惧日益高涨,他受训成为肿瘤学家和骨髓移植者,以治疗那些暴露在高剂量辐射中的患者。冷战结束后,“军队不再关心骨髓移植。”June说。他需要一种新激情。
之后June转而研究HIV。于是他了解了免疫细胞及T细胞的来龙去脉。他花了10年时间培养T细胞在HIV患者体内繁殖。
前进和争执
在宾夕法尼亚大学,June继续HIV研究,同时也投身癌症领域。他受到两位肿瘤学家的欢迎:宾夕法尼亚大学艾布拉姆森癌症中心研究成人血癌的Porter和费城儿童医院的Stephan Grupp。
也有少数来自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希望使用细胞表达嵌合抗原受体(CAR)疗法治疗患者。他们都聚焦于相同的癌症靶点—— 一种名为CD19的标记物。由于它普遍存在于一些癌症细胞中,因此该标记物是一种有希望的靶点。
但是,如何最好地设计CAR对抗CD19是个大问题。有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设计一种能够抓住CD19的新受体。一个重要的要素是“协同刺激信号”——存在于CAR细胞中,可以起到激活该细胞以及使其在病人体内保持活性的作用。Sadelain研究小组利用小鼠研究了大量的可能性,最后选定了CD28,它看起来最有希望。
June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协同刺激信号——4-1BB,实验室结果显示它可帮助T细胞增殖。小鼠实验证明它是一个有力的候选者,但并不如CD28更令人印象深刻。美国田纳西州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肿瘤学家Dario Campana领衔的研究小组设计了首个4-1BB构建的CAR。与其他研究小组不同,June还使用了残缺的HIV病毒改良T细胞。2010年,Rosenberg研究小组第一个发表了抗CD19的CAR疗法获得成功。
同样,他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,且并不友善。“这里充满敌意。”Sadelain说。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2012年7月,圣犹大起诉宾夕法尼亚大学违反了与其在2003年和2007年签署的材料转让协议。当时Campana与June分享了自己的CAR材料,宾夕法尼亚大学则认为June的CAR细胞与Campana的不同。2012年8月,诺华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开表示将联合商业化运作T细胞治疗。
那时诉讼仍在继续,圣犹大表示,Campana的T细胞构造专利申请获得批准。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声称Campana的专利无效。不过,无论是June还是Campana都不愿对这场诉讼发表意见。
跨越障碍
在诺华公司,很多人在为如何生产患者需要的个人化T细胞制定策略。他们需要确定细胞在体外能生长多长时间,因为这决定着细胞处理设备的成本几何。该公司需要采用自动化方法培养和操纵细胞,以降低成本和人为操作可能出现的错误。
“所有这些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清楚,不只是停留在美国尺度上,还要纵观全球。”负责监督诺华肿瘤该疗法发展计划的Manuel Litchman说。
一个首要任务是一致性。由于来自不同的病人,每批T细胞的质量可能参差不齐。而其他科学和生产变量——嵌入外来DNA所用的载体、生长细胞的技术,以及它们如何运输等——会使结果难以预料。
June研究小组清楚其中的困难:2012年1月,他们使用一种新载体治疗了另外3位患者,效果很差。June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甚至不知道是否载体材料出了错,或者这样的结果出于该疗法成功率的随机波动。“所有我们知道的是,它有效3次,失败3次。”他说。
Emily Whitehead是一名6岁晚期白血病患者。实验治疗使她的身体出现免疫超速。所有人都在尽全力拯救她。医生剖析了她的实验室数据,发现她更活跃的T细胞致使身体产生了过多的白细胞介素-6。最终一种关节炎药物挽救了她。
Emily度过了8岁生日。在她的DNA中,Grupp发现一种易诱发活跃免疫反应的基因突变,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治疗会使她生病。Grupp之后决定为其他儿童患者使用Emily所接受的1/10的剂量,虽然“在我内心深处,我不确定剂量应该是多少”,因为细胞会在体内肆意增殖。
迄今为止,Grupp已经治疗了14个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。其中5例曾在学术会议上报告或发表,4例进入缓解期,但之后有1例复发。Porter在今年5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成年人的相关数据,17位患者中有10位出现应答,其中5位进入完全缓解期至少3个月。
距离那个夏天已过去了近3年,所有事情都已改变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小组依然在继续工作:注册尽可能多的患者参与试验、与药物监管者讨论如何更好地研究细胞以期待获批、同诺华公司合作等。“我累了。”Porter说。他热切地等待着诺华公司开始加工T细胞和制作CAR的那一天。不过无论是June还是诺华公司都不知道到底会是哪一天,但对于June而言,那意味着回归常态。

